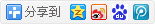著名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国人欢欣鼓舞,世界为之瞩目。这次我到了瑞典,觉得最有蕴味、最难忘的,便是莫言领奖的地方。
认识瑞典,竟是从乒乓球开始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瑞典男子乒乓球队称雄一时,与中国队平分秋色,队长瓦尔德纳尔更是世界上首位男子单打大满贯得主。
这次瑞典之行,当然不是去切磋、研究乒乓球了。莫言领取诺贝尔奖的轰动效应,如超强的情态磁场,仍然那么有力地吸引每一个游览的炎黄子孙。
首都斯德哥尔摩有“北欧威尼斯”之称,其实是一堆岛屿组成,岛与岛之间由大大小小的桥连接。这些桥没有坡度,形同平路,让人不知岛为之岛。唯见河港密布,水流奔腾,舟艇穿梭。望着流动的水,流动的城,我想起了苏州甪直、周庄的小桥流水。相对而言,前者大气魁岸,像一员健硕的欧洲武士;后者则妩媚温娴,是一位娇美的水乡姑娘。
大街上,随处可见两三中老年人,悠适地坐在路边的咖啡馆简易凉棚内,一杯饮料,几片面包。身旁鸽子起舞,鲜花吐艳;仿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时而有轨电车轻声滑过,似在与他们相互打着招呼。让人不太明白的是:在现代化程度如此之高的首都,为啥还用这种老式交通工具?节能、环保、传统风情?无论如何,车子上方蛛网似的电线,看上去总使人不大舒服。
终于赶到了向往已久的市政厅,每年十二月十日在此颁发诺贝尔奖,这一天就成了世界性的隆重节日。
市政厅位于国王岛东南端,是世界著名的庭院式建筑。门前几株合抱粗的白皮阔叶树,高大挺拔,在波罗的海风轻轻抚摸下,向我们颔首致意。
进门,迎面一座大院子。四周是三层楼高的赭红色墙体,特有的欧式落地长窗; 阳光把一层厚厚的金粉,涂抹在墙上、树丛中。翠绿色的藤蔓如章鱼的绵长触手,攀满整个墙面,留下的窗口,仿佛是它的眼睛,正热情地问候每一位来客。
讲解员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面如满月,一开口,竟是北京人;亲不亲,家乡音。熟识的语音如秧歌舞彩绸,很快把同胞们紧紧挽在一起。
随人流向左,拥进一楼蓝厅,但见庭院式厅的弧形屋顶有三十多米高,整座大厅能装得下三个篮球场。每年诺贝尔奖颁发后,这里就是举行晚宴的场所。只有如此宏旷的空间,才能容得下文明智慧检阅后热烈、隆重、喜庆的激情。
二楼议会大厅,又名金厅,屋顶呈船形。这里平时是皇家议会工作的会场,地上铺着暗红色地毯;中间是主席台,莫言就是在这里摘取了皇冠上的明珠。
讲解员得意地告诉我们:二零一二年颁发诺奖时,她想方设法到了现场,亲眼目睹了这庄重幸福的时刻。莫言精神抖擞,眯着小眼睛,双手微颤着接过获奖证书时,我的眼睛湿润了——莫言好样的!你为全球炎黄子孙露了脸。
我注意到她脸上那种诚挚、自然的表情,没有矫揉造作,唯觉真情流露。游子身居异国他乡,但传统文化的根系相连,血脉相通。心与心在特殊的境况作用下碰撞,产生了情感交融的强烈共鸣。
而莫言的获奖感言更是精彩之极。一开始他说忘记带发言稿,让人为之担心,其实这是他欲擒故纵的高明之处,恰恰体现了中国人的幽默、内敛、自信、不卑不亢。发言结束,掌声如潮,淹没了整个大厅。中华民族的黄钟之音终于在这里响起,传遍全球!金色的东方巨龙从金厅腾飞直上九重天!
我们争着用手中的相机,追寻莫言的足迹,共享久盼的荣耀与自豪。
在赭红色的主席台边上,我问她,莫言得奖后的反响和评价如何,她即刻兴奋地说,莫言改写了历史,打开了一个穿越时空的窗口,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真正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到东方文明古国身上。
莫言也许不是我国最有名的作家,但肯定是最好的作家之一;勤奋刻苦、奋力拼搏、百折不挠,他的经历再次向世人证明:成功之路就在自己脚下,中国人有能力攀上世界任何一座高峰!
莫言,已尽在不言中。市政厅大门外碧绿的草坪中,美丽的梅伦拉湖边上,一柱巨大的银白色喷泉,在璀璨的阳光下闪着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