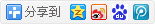成都与川内其他城市差异巨大,可以说是座不“四川”的四川城市,他骨子里的是一种怡然自乐,顺其自然的道家精神。如果说川内其他城市拟人是刚健的长江纤夫和雄健的川军将士,成都就是一个老派读书人,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大褂坐一把竹椅,品一口盖碗茶。
与粗粝的高原比,这座城市更显温柔舒适。茶馆中的氤氲缭绕,酒肆中的麻辣辛香,都令人不舍离去。于我而言,此前的成都就是一座建立在汉赋、唐诗上的大城。李商隐那句“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已令人心驰神往。来过几遭后,自然也更能理解李白晚年的惆怅——“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交通体系上,成都正在成为国际枢纽。双流机场在2014年上半年旅客吞吐量为1788.08万人,紧随北京、广州、上海之后,成为航空第四城。从成都中转出发,4个小时的航程可以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6~10小时能直飞中东和欧洲。美联航今年6月刚刚开通的成都直飞旧金山航线,公务舱与商务舱的上座率达到80%,远超预期。
成都正在从一个远离出海口的内陆城市,转变为一个国际化的城市。美联航大中华区总经理戴维斯向我们感叹,在他27年的工作经验中,与形形色色的城市打过交道,他发现与成都的合作是最流畅的:“这里的人对成都在世界上的发展前景有很强的预期,有非常超前的前瞻性。”
成都在一条快车道上突奔,对自身的评价体系正在从四川、西南发展到中国、全球。成都的崛起本质上是格局的崛起。它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一极,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一股重要的带动力量。
尽管我们能为成都的崛起找出各种现实的依据,但我们更感兴趣的还是这座城市的文化支撑力量。因为没有一种崛起是可以脱离文化支撑而存在的。
所谓文化与气质,应是一个群体所表现出来的生存态度。我同意成都画家陈滞冬先生的看法:“以成都为核心区域的四川省,在中国文化地理上是一个具有特殊位置、发挥特殊作用、产生特殊人物的地区。由于它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丰饶的生活条件,在和平时代,它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南北各地文化的营养,一旦发生战争或者改朝换代的动乱,它便会立即发挥出文化蓄水池的作用,输出文化,以使中国文化的历史不致断裂。”
几千年来,虽地处国之西缘,成都却一直源源不断吸收着中华文明的营养。以其宽厚包容的精神,接纳着往来的过客。今天去杜甫草堂,可以看到杜甫、陆游与黄庭坚同堂供奉。陆游与黄庭坚是学杜有成开宗立派的大诗人。他们与杜甫一样,虽非川人,却都流寓蜀中,并没有受到冷落。诸葛亮、浣花夫人亦如此。
自秦始皇横扫六合,打击关中豪强,肃清异己文化,便将程郑、卓王孙一类经营有术的富豪赶往巴蜀,又将“不尊先王之法,不循孔子之术”的吕不韦及其门徒流放进巴蜀。外来精英的融入,直接推动了西汉巴蜀文化的崛起。汉赋四大家中,司马相如、扬雄、王褒居其三。及至唐代,自安史之乱后,中原动荡,掀起了“天下诗人皆入蜀”的盛况。典章书籍、百工技艺,都随着移民次第进入成都,成就了晚唐两宋的社会盛况。
近代成都,更是一个经历了“湖广填四川”后形成的移民社会。多元文化在成都这个大熔炉中激荡融合,使成都人的精神世界格外丰富,从而展现出一种多姿多彩、内涵丰富的城市气质。就像谭兴国先生分析李劼人作品时的说法:“这种氛围熏陶习染的结果,形成了一种特殊性格和精神气质,它若以圆滑、乖巧、狡黠、灵活、机智、八面玲珑、自由主义、乐观主义等等而言,似乎都不够准确和完整,又似乎正是这些形容词的综合才能道其神髓。”
成都最近的一次文化高峰,便是在抗战时期。因华西协和大学的存在,华西坝吸纳了大量内迁高校。一时间,名家大师云集。文有吴宓、陈寅恪、顾颉刚、钱穆、蒙文通、吕叔湘等;理工有刘恩兰、赖朴吾、魏时珍、李晓舫诸先生;画家有张大千、傅抱石、黄宾虹、李可染等。当时每年成都的画展就有300余次,以至于张大千说:“中国文艺复兴的时期到了,地方就在成都。”
另一方面,“边缘意识”又使成都人保持着冷静的独立性。愈是社会风云激荡之际,愈能激发活力与创造精神。如大汉声威之于司马相如、扬雄;盛唐气象之于李白、陈子昂;晚唐夕照之于韦庄、赵崇祚的花间丽词;“五四”浪潮之于郭沫若、巴金;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之于周克勤;现代艺术狂飙之于成都画家群。
成都人身上因此展现了一种殊为可贵的独立姿态——不跟风、不盲目,不追逐标签,不为时髦而时髦。如李劼人在1949年开始潜心撰写地方志《说成都》,天下鼎沸之际,却事此不急之需。画家陈子庄,于70年代艺术跌于低谷时,闭户绘画,以破箱子代替桌面,仍不断开拓中国画的新局面。
包容与独立成为成都文化气质的两个支点。成都的可贵,一方面在于保留了那些精致、富丽、温文尔雅的趣味,以及普通人对生活品质的热烈追求,另一方面,则在于它能不断自我更新,吸收新知识,接驳新的时代精神。虽偏离中心,但并不甘居边缘。于是,在每一个大时代来临之际,我们总能感受到成都的活力与魄力,与大胆的锐气。
2000多年前,成都才子司马相如在《难蜀父老》中写道:“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今天,这种执著于“非常”的雄心、气度,仍深植于成都血脉中,使其自励而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