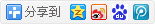因为照相机没电池,只好把计划中的“印度文化+甘榜格南伊斯兰文化”分成了两截,除了更从容之外,内容还有所增加,临时的权变有了别样的收获。大年初五的下午,也就是我离开新加坡的前一天,接着植物园的行程,坐巴士到多美歌,从总统府门口过去,换了一趟巴士,直抵中央锡克庙。
在“places of worship”中,这里被称为“sikh gurdwara”, sikh锡克不是种族的信仰,只是信仰者的自称,他们的共同信仰便是sikhism锡克教。所谓锡克教其实是非常晚近的宗教,源自于印度北部,最典型的标志是男人头顶上的大朵头帕,在新加坡到处见到黑黑的印度人,但只在中央锡克庙前见到一位缠头帕的锡克教信徒。
被称做锡克庙的gurdwara实际上是“谒师所”,锡克教不拜偶像,只拜经典,“谒师所”就是存放经典之所。信徒们来到这里,面对存放经典的祭台叩头奉献,然后大家一起打坐诵经。锡克教比较强调信徒之间的结盟,强调不分阶级,团结友爱,甚至男女兼收。
朋友的丈夫有点开玩笑地形容锡克庙是葱头,为什么不这样形容清真寺呢,可能这里的清真寺理较少这种形状吧。不知道为什么锡克庙的形状有点像我们常见的清真寺、东正教教堂,甚至蒙古帐顶,莫卧尔王朝就是蒙古族统治嘛,那正是锡克教兴起的时代,兴许有些关系,尽管锡克教一直在反对蒙古族统治,但文化上的学习和借鉴谁说得准呢。
中央锡克庙在陶纳路(towner road)和实龙岗路的夹角上,跨过陶纳路,沿实龙岗路向南,很快就看到一幢占地面积很大,但却只有三层高的建筑,便是曾经住过这一带的朋友说的“(中央锡克庙)旁边是一家医院”,这所医院叫做“广惠肇留医院kwong wai shiu hospital & nursing home”。广指广州、惠指惠州、肇指肇庆,这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英文的拼法不同于现在的习惯罢了,hospital是医院,我还是认得的。&后面的nursing home是“什么家”,当时我想,对照中文“留医院”,我琢磨着:应该是能够留病人住院的大医院,而非只应该门诊的小诊所。
回京后,认真查了一下,原来其中大有学问:此间三属热心仁翁善长合资创办于百年前的纯粹民间慈善医院,原仅限于为同乡提供医药上的完全免费服务,至1974年才打开大门,不问肤色、种族和籍贯,男女老幼病黎都一视同仁,造成费用日重。医院的义款来源主要为基金会、寺庙,或者个人的捐助,应付庞大开销,在筹募义款方面,广惠肇留医院大有办法:节日庆典、商号开幕、病人康复等馈赠花卉、花篮换得捐款,印刷贺年片等供人购买,动员学生及义务工作者于售旗日到全岛各处售旗筹款,派募捐小组到各商家、购物中心、地铁站、小贩摊挡等沿户募捐,参与各区酬神宴会……
所谓“留医院”,在中国首创者为广东的梁培基,他仿照日本“旅馆医院”的模式(医院设备齐全,有固定护士,病人入院,可在市内自由选择医生,邀请到院诊治,全市医生也可介绍病人入院,由自己继续诊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广州的二沙岛建珠江颐养园留医院,所以我想“留医院”这个名字当是梁氏所译。另外网上有介绍美国的nursing home:是给那些家中无人照应(通常自己有保险,多数是残障)的人提供的“家”。护理院里通常由许多护士助理(nurse assistant)及护士组成的队伍来管理,医生定期来检查。梁培基的“颐养园留医院”服务者富且贵者,美国的nursing home键是要有保险,这与“广惠肇留医院”简直云泥之判了。
再向南就是劳明达街(lavender street)了,左转后不久,地图上有一条斜道可抵惹兰勿刹(jalan besar)路,这条路很短,我自认没问题,见到一处食肆,正在中午,也想体会一下,便要了一碗鱼圆冬粉,已经初五了,店都开了张,不少老人独自在这吃饭。
吃了饭出来,转不到惹兰勿刹了,转了两条街,忽见前面蓝天之下,红黄白绿的经幡飘扬,走近一看门楣上的装饰颇具藏式建筑的风格,正门匾额题“大乘禅寺”。实在没有想到这佛教的各分支与基督教一样都瞧中了新加坡的这一亩三分地了,这里的位置靠南,早先看到的佛牙寺、千光寺,都极尽南传小乘的气派,突出的特点就是干净,脱鞋、供花、不点香,的确少人间烟火的气息。熟悉的烟火气来自粤海清庙、大伯公,这回终于看到一处点香点蜡的佛寺了。印度是buddhism佛教的发源地,但这印度人来到新加坡,建了锡克庙、建了清真寺、建了兴都庙,偏偏没搭理佛寺,可见佛教在印度式微到了何种程度。
倒是外传的佛教得到发扬光大,据说阿育王推广原始的佛教,使佛教四下传播。经由斯里兰卡为中心并把佛教传到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南亚、东南亚各国,还包括中国的傣族地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南传佛教,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小乘佛教;由北印度经新疆传入中国,并由中国传到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家的佛教,相对于南传佛教叫做北传佛教,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大乘佛教。藏传佛教是从古印度和中国内地传入西藏地区的佛教密宗与西藏当地的古老宗教融合而成的具有西藏地方色彩彩的佛教,俗称“喇嘛教”。
“乘”读为“shèng”,方便的解释是大船、小船,大乘载的人多,标志度众生,南传的小乘则只重自身修行,可惜在大乘看来只顾惜羽毛,被称为“自了汉”,不过他们自己从不称“小乘”,并视之为贬称。这处以“大乘”为名的藏传佛寺不仅证明了新加坡的佛教信仰者以小乘为多,应该更是标榜自己的功德力量。中国的藏传佛教寺院也都是大院子的,新加坡地窄,就一间,宣传品都插在门外墙上的廊下,初一至十五的活动排得满满的,庙前的高香粗壮地点燃着,还有香炉,倒是五脏俱全,没这信仰的我倒没有勇气进去参观了。绕过庙前的香炉,对街角白生生的一座教堂。
问人找回了惹兰勿刹,besar和新加坡著名的食肆老巴刹lau pa sat,中英文都有些出入,但明显都是音译,想起摄影家们在新疆都爱拍的“巴扎”,据说是维吾尔语“市场”,我怀疑都是阿拉伯语的转音,这地方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也蛮大的。而这一路走来,南洋魏氏公会、客属黄氏公会、江西会馆……原来新加坡不只牛车水,华人也是遍布啊。
江西会馆对面有一道排水沟,几天没有下雨,水泥的沟帮沟底都露了出来,顺沟向里一望,一块水泥平板搭在排水沟上,上面两道扶栏,迎边挂着红匾黄字的繁体右排的“
沿jalan sultan一路下去,过向北拐的梧槽运河,就进入了甘榜格南(kampong glam)地区,词的来源:kampong是马来语“乡村”的意思,glam是一种树汁入药,树皮能塞船板缝隙的树。这一带是马来人的聚居地,又是阿拉伯商人的活动区,伊斯兰气氛浓厚,baghdad、bussorah、kandahar(拼写完全一样,或者小有差距),这些个地名熟悉吧,如今美国的伊拉克、阿富汗两条战线,天天电视新闻里都在念叨这些地名,在此,新加坡都是街名!
甘榜格南的开始就是河畔的malabar mosque,它守在街角,背后一片绿地,据说河边是原来马来人的坟场,不知道当年的迁坟运动有否触及到这里。这会儿正是下午上课的时候,清真寺边上的一位女子学校的姑娘们正在进教室,遥遥地望楼上走廊里披着白色头巾女孩,晃如天国。
过了甘榜格南民众俱乐部,便是哈惹花蒂玛清真寺,正是做功课的时间,空气中充满了召唤声,男人女人都在向哈惹花蒂玛清真寺去,男人进去,而女人则站在寺外。两个街区外的马来王宫墙外,几个上学路上男孩引来过路的成年人的微笑,这座已经改为博物馆的王宫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怪不得朋友的丈夫说,那没有什么可看的,院子里时时有上学路上的孩子跑来跑去,他们能够在自己的文化中成长也应该算是一桩幸事。
毗邻的masjid sultan苏丹清真寺(一样的清真寺,不用mosque,却用masjid,而纳哥德卡殿又用了shrine,难道用习惯用法能解释得了吗?)前两侧都是纪念品店,多几分旅游点的意味,但在寺前,有一对看上去像父子似的信徒,在用手机照像,之后向我请求,虽然听不懂(连说的什么话都判断不出来),但比划着能明白。one、two、three之后,把相机递过去交作业,两位穆斯林彬彬有礼地道谢,在这里的确没有中国境内的异样感,地铁、汽车上,大家彼此也都靠着很近。
沿着arab street向西直奔梧槽运河,前后走着、跑着上学路上的学生,穿着校服的伊斯兰男校的学生,头顶小黑帽,白衬衫蓝裤子;而女校的学生,则是黑色长裙,上面的头纱是一个成型的套,将将把脸露出来,后面披满后背,前面垂在胸前,左胸前绣着校徽,可惜没好意思照人家的正脸。
过河沿河边的双溪路(sungei road)向南再转西,拐角处是森林大厦,一处大门口台阶边正圈出一块平台做个小庙,往来拜拜的人还真不少。照理这块儿已经是小印度了,应该以信仰印度教的人群为主,但实际上,我先遇到的是阿都卡夫回教堂abdui gaffor mosque远远就望见,比起之前的清真寺,它可算是最光鲜的一座清真寺了。不过与苏丹清真寺属于马来人相比,这座阿都卡夫回教堂倒是属于印度回教徒的。
印度人的信仰真是丰富,与中国一样南部人移居海外的多,也带着他们的信仰。比如泰米尔人(tamils),我们常听说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的那个“泰米尔”,是印斯两国都有的民族,新加坡叫“淡米尔人”,不少,四种官方语言里都有,他们主要信仰印度教,实龙岗路上的斯里尼维沙柏鲁玛兴都庙(我看到边打电话边进庙的一对夫妻的那座兴都庙)是泰米尔印度教教徒修的。而同样来自南印度的朱利亚人(chulias)则信仰伊斯兰教,这些移居新加坡的穆斯林是最富于冒险精神的商人、货币兑换商和贷款商,果然是中国人说的“憋宝回回”,牛车水的詹美回教堂、直洛亚逸的阿布拉回教堂和纳哥德卡殿都是他们建的。
照着在仰光路上观音庙前的妇女的说法,再往里起果然是印度教的地盘了,穿着沙丽的妇女穿梭在小摊之间,瓣瓣朵朵鲜花、香蕉、绿叶重叠在一起堆成花环花盘,引来蜜蜂,大人们熟视无睹,但跟着的女孩却左闪右躲。在新加坡见到的印度人大多是印度南方的,特别是妇女穿传统服装都是沙丽,我曾在义顺组屋前的一座小桥上拍到过一位身穿沙丽老年妇女,当时天色已晚,我走了一天有些累,从后面追赶,眼瞧她将下桥了,急忙按了快门,也是学艺不精,模糊了。但舍不得删,如果在小印度之类的地方就算了,在义顺这样普通的居民区,仍有保持传统如此的人,着实让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