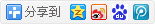悠扬的笛声响起,巨大的圆环如一轮满月降落在舞台上,彩衣少女在环中翩翩起舞,美丽又高难度的动作引来台下一阵阵的喝彩和掌声。这个周末,《平凡与梦想》蜀韵杂技在四川歌舞剧院里上演了,这是原成都市杂技团经过改型、转制后的第一场演出。美轮美奂的场景,惊险刺激的技艺,一个半小时的杂技专场让观众大呼过瘾。
老艺术:
观众:
和记忆中的杂技不太一样
上周五晚9时30分,《平凡与梦想》的第一场演出圆满结束,意犹未尽地离场的观众中,记者听到最多的赞语是“不一样”和“真漂亮”。
“感觉杂技就是以前看电视上的那种,很惊险,直白地在展示技巧,没想到能做得这么漂亮,确实好看。”观众廖女士说,这场演出让她很惊喜,也改变了她对杂技的印象,她6岁的儿子已经彻底被迷住了:“—结束就跑到台上去,还往幕布里钻,以后还有这种演出,我肯定带孩子去看。”
除了精心设计的舞台布景和灯光音乐,在《平凡与梦想》中,杂技技巧与成都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让成都入看着分外有“亲切感”。如男子钻圈《青城道》融入了太极和武术,充满节奏和力量感;草帽杂技《蜀乡秋韵》展现出川西汉子的热情活泼;双人吊环《凤求凰兮》表现了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缠绵而华美;《思凡曲》的音乐和服饰都有浓郁的川剧元素,特别受女孩子喜欢;至于双爬杆《熊猫戏竹》就是小朋友们的最爱了,演员们全都穿着毛茸茸的熊猫衣服,憨态可掬的样子让现场笑声不断。
演员:
我觉得台上的自己美翻了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在杂技演员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成都艺术剧院杂技团里,演员们的年纪平均不超过二十岁,最小的一位今年只有十五岁,完全是一群“90后一,但他们最少已经练了十年功夫了。“我是从s岁开始练的,国里的最晚也就是8岁开始,学这个要趁早,超过l0岁就没法练了。”邵科立出生在杂技世家,别的孩一子还在无忧无虑地玩耍的时候,他就开始跟着师父练习“倒立”,就这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他练了十多年,每天至少8个小时。“要练到倒立和直立没有区别才算是过了基本功,其实,所有的杂技技巧都是这么慢慢磨出来的。”
个人技术要过硬,和伙伴们的配合也很重要,由13人共同完成的男子钻圈《青城道》就展现了他们之间惊人的默契。今年19岁的黄思源说:“我们都在一起呆了10年了,彼此熟得不得了,一个眼神就知道该怎么配合。
”练杂技很苦,很累,很枯燥,团里有很多同伴来了又走,而坚守到现在的他们,都抱着一腔对杂技的热爱。《凤求凰兮》的女主角宋思思就很自豪地说:“我喜欢在舞台上的感觉,表演的时候,觉得自己美翻了!”
新梦想 杂技更美丽 却不再让人揪心
小演员们在休息的时候,几位跟团的老师总是忙着给他们补妆、提醒演出的注意事项。他们都曾经是杂技团演员,而且是入行二十多年的老前辈。说起自己的杂技团,他们满满都是骄傲:“1984年我们去了第23届奥运会,香港回归的时候也有我们的表演,我们还是第一个进入台湾的大陆艺术团。”杂技团老师黄鹦说。
辉煌过后
杂技团一度陷入低谷
可随着时代不断改变,观众的审美变了,辉煌一时的成都杂技团也陷入了低谷i愿意练杂技的孩子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断代的情况。在《平凡与梦想》以前,成都已经多年没有本土杂技团的演出了。
“我们有一次在国外演出的时候,一个老外看得当场心脏病发作了,直喊着让我们别往上叠了。”黄鹦说,和她一代的老杂技人都经历了那种为了追求技术难度的“残忍”训练,那时候的杂技,是“让人揪心的美丽”。“练顶碗就一定要练到头发都磨光,那会儿如果做不到这个,都不算入行。可是练得这么苦,甚至满身都是伤,却不一定好看,观众也不买账。“
重新编排
杂技更美更吸引观众
《平凡与梦想》总策划唐静说,他刚接手杂技团的时候,排出来的节目和十几年前的没什么两样,“这些孩子们表演的时候嘴里还喊着‘一二三’,根本不会去听音乐,刚开始排《平凡与梦想》的时候,还对舞蹈老师很排斥,不过现在他们都适应了,也有‘演员’的感觉了。”如今,成都艺术剧院杂技团淘汰了一些不必要的、对演员伤害很大的高难度技巧,重新编排剧目,并计划将话剧也融合进来,让杂技变成一种更美、更有故事、吸引观众的艺术。
在这群杂技人的眼中,《平凡与梦想》是老艺术的一次全新的尝试和创新,黄鹦说,在首场演出上,很多早就转行,甚至出国了的成都杂技人纷纷赶回来,一起看了这一场演出。“我们看到了杂技艺术的曙光。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剧院也为杂技演员安排了以后的出路,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孩子愿意投身杂技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