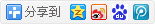早上7点40准备好一切,出发,仍下太子站D口,不过今天是向北去,乘两站在九龙塘换东铁线,钻了个大山洞,过去就算是香港的郊区了,这是从广州来时就发现的。东铁钱直抵罗湖或落马洲,要过界者需认真听清。我要到的地方距离罗湖和落马洲都是一站——上水,还属香港地界,以为无需关注,没想到这条线跟北京的公交车似的不少“区间”,我乘的这趟车在大埔墟就算到了站,把大伙都赶下了车,全在站台上等下一趟。
好在我只到上水,无论到罗湖,还是到落马洲的车都可以上。说实话离开了繁华的港岛和九龙,香港的人还真的不多,虽然无座,但空调下不至于难耐,无须多花一倍的钱去头等车厢。港铁只此一条线有等级之分,不知道为什么,看到有人在标志头等车的位置等车,或者上车后,用八达通在头等车厢关着的门前一拍便开门进去,仿佛那边人人有座,如此而已。近来大陆的动车好像也都有了一等、二等的,所以叫个“和谐”号,如果平等,倡导和谐也就无意义了。
上水下车,一处蛮繁华的所在,想来与新加坡一样,每个地铁站周边都是一个硕大的小区。拿出地图册,来之前已经做好的功课,可步行亦可乘车,大早上的走走没什么(主要是攻略上写了约15分钟),便核对了方向迈开步。然而上了天街又犯了难:无数的楼梯下哪个?问人,天桥上除了匆匆的行人,就是遛早的老人,也提笼架鸟的,真是热情,普通语说得也不错。下了天桥,没问题了,有街名,有游览特别的标志牌,紫色的,昨天在街上就遇到过,不远一个,很实用。别看到了乡下,这一点香港做得一点也不差,我就是顺着这个指示,直接寻到了要找的万石堂。
万石堂,在地图册上和当地的旅游标志的英文都写作“Man Shek Tong”,其实这个“石”字,是粮食的量词,读作“dàn”,堂名来自该姓氏在北宋时的显赫祖先事迹,据说当时这位祖先和他的四个儿子皆任高官,每人俸禄各二千石,合一万石。不知道是粤语里没有“dàn”的读音,还是翻译者随意按照字形最普通的读音来译。
万石堂是上水廖氏最大的祠堂,位于上水港铁站的西北,一路走上去,一点也不像是农村,而像城市的效区,马路平,标志齐,树木茂盛,地貌经过修整,更重要的是沿途不间断地安插着彩旗,都是庆祝国庆60周年的,简直和北京一样嘛。另外,汽车多,处处都是停车场,没有一点农田。
终于可以拐下马路进村了,乡村里的房屋虽不像港岛、九龙那样高拔,但也是一幢幢的小楼,排列也还算整齐,之间都是柏油的道路,而且许多水务局正在挖地的设施。这次香港之行到处是一样的高涨的建设热情,一点看不出经济危机,更有趣的是即使港岛的大街面上十几层高的大楼,外面的脚手架都是毛竹的,这在北京根本看不见,都是国家标准的钢管拼接的,由此也可见香港人是很“保守”的。大榕树下有几张固定的长椅,几位清洁工正坐着休息,问路,一指,果然前行几步侧头便在小楼后面瞥见了。原来应该是村落的核心和标志,现在祖先的所居已经被后代的所居遮掩了。
正好9点,一位管理员正在开大门,我来得正是时候,只有我一个游客,女管理员也是无聊得很,热情地和我聊天,奇怪的是她真的一点普通话也不会讲,全凭我猜,但能听懂我说的普通话,比如我说:“噢,你住在元朗。”她嘿嘿地点头,可不是像日本人那样,我怀疑这客家话与我老家的莆仙话有相近之处,莆仙话在应和别人、赞同别人时,发的音就是“嘿呀”。
不知道是因为有点适应了,还是她说得慢且重复并尽量用最简单的词汇,我还真的能够明白点:她属于威智护卫公司(当然她穿的制服上有“威智”二字),政府向他们公司雇人看守这些古迹;她住在元朗,有班车(这点有疑问,可能说的是公交车)过来上班;她没有到过北京,但知道万里长城;这个村里的人都姓廖,平时不来这间祠堂,到过年时会用这里举办全族大宴。
万石堂里空空荡荡,只后厅的后墙上排着祖先的牌位,密密麻麻,有些裸放着,有些放在小龛里。牌位才是传统,现在不知道跟哪儿学的,总是造像,佛教还是基督教?原来孔庙里都是牌位,现在非得塑个孔子像,为此还要颁发一个标准,以便全国统一,让孔子在国子监看着大门,怎么让人心安,哪里有尊孔的意思呢!看传统到香港!我想。
过厅的墙上挂得老高有一块已经斑驳的红底金字的匾,中间的字大“文学士”,边上的小字看不清,用我的傻瓜相机拉到最近照下来,再放大了看,上款是:上水村族长廖瑞祥为,下款是:一九六一年香港大学二级甲等荣誉文学士廖庆齐立。也可能是“廖庆斋”,照得不清楚。记得老家的祠堂里挂着当年各支派新生男丁的报到贴,与此大约相仿。
蒙管理员相送至村中一条小巷口,我问她马会道怎么走,因为那里有汽车可以回上水港铁站。走不多远是一株被红墙围起来的大榕树,围墙正对着一个围门的那边向里窝进去一点,便是土地老爷的神主之位。围门已经是水磨磁砖翻修过的,朝外的一侧刻松鹤,对联是:龙腾凤水,虎啸鳌山;向内的一侧刻的是兰石与牡丹或是菊花,对联是:敦诗说礼乡称善,祗父恭史里有仁。足够传统吧?可惜围里围外已经都盖了楼,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了。
下一站是粉岭站东北的粉岭围,如果回到上水站要坐一站港铁到粉岭再走,但我感觉这两站之间没多远,在又一处几株榕树、几条长椅的地方问闲人:没多远就是天平村,20分钟就走到了,天平村对面就是粉岭围。的确地图上也是这么画的。朝指的方向走,到村口,又一个休息处,香港政府挺会来事,一个村里,修了两条长椅便称某某村第几休息处,好像时时提醒村民:是政府给你建的呦!
不知道怎么就走错了,人家还特意告诫我要向左的,但偏偏我就向右了,结果走回上水站,没坐车,索性沿港铁线的新运路去粉岭,地图上粉岭围就在这条路的边上。要说也不近,加上我的犹豫时间,走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才找到我要找的彭氏祠堂。粉岭围紧靠着新运路,村口的风水塘还在,已经修得非常整齐,周边是空场,正午11点多,太阳正毒,村口的人说祠堂还要向里去。及至祠堂已经望见马会道了,书上在北便村,地图册上写的是“粉岭南围”、“粉岭正围”、“粉岭北围”,我想应该是在“粉岭北围”吧,看来从上水乡出来的确应该照着人家说的向左走马会道为妥。在村里看到人家写门牌为“北边村”,这比“北便村”更为合理。
彭氏宗祠“商贤世泽,宋史家声”的对联和两个门神还算鲜亮。商贤是不忘远祖,而宋史则指本支来自江西的彭俞一支,我看过几本家谱,远祖大多挂靠显耀,中断多代,然后才是一脉相承,相信由宋以下的记录是真实的,因为自范仲淹开始大力推行民间修谱。门神看得清晰,是因为大门紧闭,可攻略上说上午9点至下午6点是彭氏宗祠的开放时间呀,坐在门两侧的高台上想等个人来问。
“正晌午说话,谁也没有家。”就是我此时的状态,半晌来了一位,先观察一下,乐了:此公五六十岁,穿一件薄T恤,更显得胸前和背后隆起老高,偏拿了一只盛着水的大可乐瓶,来给祠堂前的两株种在盆内的小树浇水,哈哈哈,柳宗元的《种村郭橐驼传》!那是古文里读的,能见的形象是戏台上《牡丹亭》里柳梦梅的仆人,说是郭橐驼传下驼孙嘛,可惜这是彭氏宗祠,若是柳氏的那真要大叫“真实”了,柳梦梅不就是居于广州吗,到香港很近了。
乐归乐,正事还要打听,上前问:不开放旅游吗?他好像并不理解我的本意,回说:新年才开。我明白说明上错了,或者说人家现在变主意了,仍归宗族实用,不理会观光了。从门边贴的符看,从门角仍点着的香看,的确彭家人仍在照顾这所祠堂,与外人无涉。
村口有一所小院是“思德书室”,而院门却写着“粉岭学校”,好像也关了,可能迁往更正规的校舍。学校对面是一道铁丝网,上面挂了两块粉岭村村公所所示的警告黄牌。一是“严禁收买佬进入本村范围活动,如被发现,送官究办。”一是“本村范围已安装网上闭路电视监察系统,你们的一举一动已被监视,我们坚决将不法之徒绳之于法!”口气怎么跟文化大革命似的。
又走了40多分钟到龙跃头,横穿过粉岭,但好像不是繁华区,人少(也许是正午12点半吧),尽是工厂和仓库。香港的康乐署负责区内的文化事业,其中文物保育是重要的一项,“保育”一词仿佛与大陆所说的文物“保护”有所区别,“育”既有文物本身的养护,也有文物对后代的滋养,而“文物径”就是香港政府推出的很有特色的一种教育方式。大陆常说旅游线路,听着就是做生意,而文物径则不同,由政府和业主共同认证、确立,政府负责规划、宣传。
过一道小桥,龙跃头文物径正式开始,首当崇谦堂是一所教堂,又是巴色会的,昨天在筲箕湾遇到过,不过规模远远不如,说因教友邻近聚居而成村,但我没看出村落的样子。走了好远,有些空着的农田,路边的野草相当繁茂,见一株在办公室里养得半死不活的绿植在此地叶阔且肥,甚是欢喜,急忙照下来,回去给同事看。
龙跃头文物径1999年开放,以此地曾有龙跃其间而得名,始建于元末,新界大族邓氏在这里共建五围六村,形成庞大的家族势力,虽然他们也很配合政府建立文物径,但介绍中有不少景点明确说明“私人物业,不开放”,只允许外观。比如建于1925年的石庐,因其风格中西合璧,建筑人亦为知名人士而定为该文物径上的一处景点,但距他几十米远的路边就是一道爬满了野蔓的篱笆,简陋的门上写着私人物业,向里眺望是一幢很破败的石房子,肯定没有人居住,但人家就是不让你近前。
再往前,是围墙尚在的郁葱围,这是围门上写的字,但因靠近麻笏河,人皆称麻笏围。黑色的围墙与围内新鲜的小楼拥挤在一起,仿佛要被撑破了。门洞里的荫凉里,一个年轻妇女带个小女孩,过去搭话,那妇女说她不会说普通话,也许是不愿与生人搭话吧。本想逗那小女孩开口,围外来了一辆中巴,是接孩子上幼儿园的,香港这地方怪,孩子怎么下午上幼儿园呢。
离麻笏围不远有一处竹园,外面是铁丝围,写着军队用,见我徘徊于此,里面出来一个妇人,问我上不上香,我说:不是有军队,还是不去为好,她却说:军队是保护我们的。想想也是也是解放军嘛,人民的军队。
小径果然不如大道,只能容一辆车,错车处恰有一处住房宽绰的土地,这还是很少见的,土地庙一般都是小小的,在树根下,墙角边,这里却为他修了一个大平场,官帽座也挺大,但不恭敬地说,如果没有那尊土地公像,怎么看都像小时候住平房时,一片房子共用的垃圾场。有土地庙就有人,果然老围到了,虽然康乐署的介绍中说为避免对居民造成滋扰,老围内部不开放,但我还是迈步上了台阶。一探头吓我一跳,一条大狗趴在门洞的荫凉里,定晴看到大狗的后面还有一个土地龛,拿出相机照相,那狗根本不搭理,不过我还是颇有自知知明地退了出来。
老围外便是天后庙和邓公祠。据说南宋皇室南奔,有宗室女嫁与邓氏族人邓惟汲,其长子于元朝末年迁居龙跃头。这座祠便是为纪念开基祖邓松岭公而建的,郡马邓惟汲及皇姑赵氏的牌位居中,雕有龙头,不过我进去的时候,看上去刚刚吃完午饭的管理员就说要关门了,中午休息,是啊说明中写了下午1点至2点是不开放的时间,只能向外,后面是厚重的木制大门关上的声音。
路走得不近了,但这条线还不到三分之一,我打了退堂鼓,毕竟两个围村看下来挺失望。正好邓公祠前有小巴回粉岭火车站,便坐在大树下等车,头回坐小巴,边上是一位孕妇,能说普通话,一路指点我拍卡,下车,进东铁线。直接坐到尖沙咀,算了一算,从粉岭等车、换车一路过来是两个多小时,如果坐上地铁,两头各伸一两站,深圳的罗湖至香港的中环,2个小时没准都用不了,真是可以住深圳而在香港工作了。
上来正是九龙公园南端的海防道,找福德祠,进了门却不见正殿,沿着小巷转两道,好像是在两边建筑之间搭起顶篷的感觉,门口边就是焚化祭品的葫芦炉,再拐了两道才见了正神,“殿”里七七八八的杂物,还有衣冠不整的看庙人,这是我见过的最不成体统的香港寺庙。退出来已是又热又渴,带的水已经都喝完了,用八达通卡在7-11店里买了两罐饮料,坐在九龙公园一处圆形的石柱间休息,旁边是几位印裔青年在聊天,公园的喇叭里反复用粤、普、英念着禁止点蜡、烧纸的公告,想起头天看到的公益横幅:画的是中秋夜沙滩上燃着的蜡烛边,一家数口吃惊地向上望,上面嫦娥模样的美女在摇手,汉字写的是“煲蜡违法”。
沿弥敦道向南去海边,望见对街是很多人游记里写到的重庆大厦,那楼上的招牌竟是“重庆超级招待所”。坐是天星小轮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乘船的人不多,真正当成交通工具的怕已不多,大多是我这样观景的,从尖沙咀至中环,再坐回来。那船的条椅靠背有趣,能够前后移动,这样两排相临的椅子既可以如课堂般排排坐,也可以让你面对面促膝而坐。如果说此行没有算好的话,这一天有点冤,虽然不贵但坐了一个来回,还是有点可惜。
尖沙咀沿维港一侧都是现代建筑,下小轮从西向东,正与半岛酒店面对面,当年香港的日军就是在这里签下的降书,可惜它背后的那幢高楼把个半岛酒店整得像太师椅的一对扶手,香港太逼仄了。回到弥敦道,向北在街的两边串,因为在同侧根本无法拍到建筑物的全貌,先是九龙清真寺,再是圣安德烈教堂。教堂对面是高大的榕树,一个男孩拿了皮尺在量,我问需要帮忙吗?他客气地回绝,然后在纸上写。
“是在做作业吗?”我估摸着是高中生的自然、科学、乡土一类的课程作业。“什么题目啊?”
“是《树木与环境的关系》。”我吓一跳,这么大的题目。
“是一个小组一起做吧。”我想他们是分头进行的。
“不可以,是毕业论文。”啊,是大学生啊,人家已经三年级了,学地理的,要做一百多棵树,此周围有六十多棵,另外就比较远了。想当年我也有志于学地理来着,因为文科考试里有一门地理,便以为地理系属于文科,等报名时发现地理竟属于理科,只好考中文了。于是我问:在香港,地理属于文科还是理科?他想了半天:属于社会科学。
弥敦道两侧不是金店就是银行或百货店,我是没有兴趣进去,佐敦道口向东有一个童军总会,打算看一下,这基督教意欲覆盖整个人群,有什么男青年会、女青年会,连小孩子也归入童军,后来的政党也有样学样,有青年团,还有少先队、童子军之类,不过名字不同罢了,处处是组织,没有了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随意。果然佐敦道地图标识的位置是一所教堂,但没有中国字,长相稳重,有一个碉楼样式的从属建筑,与后来在楼梯街看到青年会很有几分相似。5点半过后,我进入庙街地界,一路走回太子,重温初到香港的第一天:
中午酒店Check in完成,天正热,要躲过去,休息一阵,吃点东西,大约3点钟出门,目的地就是庙街上的天后宫。从地图上看,就是太子、旺角、油麻地三站,从3点至天黑,逛个来回,时间应该是富裕的,于是信马由缰沿砵兰街向南去,不过很快就跨过了弥敦道,经过一串有着很生活化街名的街道:西洋菜街、通菜街、洗衣街、黑布街、白布街、染布坊街、豉油街等等,街上一片一片的修车行、跌打诊所,大约集中在一起好做生意;还有教会学校正是放学时分,水月宫、福德祠里盘香朵朵;小街的中心站着个加油站,油库难道在地下?小街上没有人行道,但路口写着“LOOK RIGHT望右”或者相反,同时画着箭头。
沿豉油街转向弥敦道西,一连多少家是卖佛龛的,什么天官赐福,什么土地,有大有小,有简有繁,结构各异,都是刻着金字,间或还有棺材铺,中西棺材一应俱全,不好意思照相。有一处公共建筑与其它不同,它是做买卖的,但是独立的、坡顶,前面有马头墙,上面有匾额,刻着“秀和栏”,估计是较早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市场。“某某栏”这或者是香港、广东一带习惯的称呼吧。不远处大厦底商,是一排果栏:广丰、建明、东记、广隆等,都称果栏,门里门外都是水果箱,也许某某栏专门指批发店的。
终于看到天后宫了,前面是一片市民广场,大榕树数株,门楼一座,条凳上坐满了老人,一望便是当地长者,也许是时间较晚,也许这里不是观光的地方,总之游人少。天气不好,一阵一阵的下雨(在香港来头带尾7天,只这半天下了阵雨),树下更是黑影泛起,天后宫正准备关门,匆匆转一圈,也去坐到他凳上,看榕树的气根,看栅栏里都已掩上门的天后宫。
说是天后宫,实际上是一组信仰性建筑,从左向右数过来:观音庙、城隍庙、天后古庙、观音楼社坛、书院,其中主庙“天后古庙”居正中,左右各有一小跨院,院门上题“步云”、“留余”。城隍、社坛,是保一方的神祗;天后提供沿海渔民和居民精神保护的重要力量;观音不用说救苦救难之外,也为了祈求更多的繁衍;有生就有育,书院提此重任。他们构成一个社区全部的公共资源,前面必有平场,供社区集会、信徒崇拜之用,这叫集体办公,资源共享,一炷香,一趟路,就齐活,在小城市大多如此,这一带估计也是香港雏形阶段的一个细胞。
任务完成,打道回府,用不着顺原路回去,因为香港的街道太多了,围绕着天后宫,都是卖小商品的小店或小摊,一些早出来的摊子已经在摆货了,不过购买者还没有。我视而不见地穿过去,倒是街边的歌厅、麻雀馆等吸引眼球,还有什么泰国指压,这一带大约是声色场所,我这么想。一家麻雀馆外,灯火灿烂,金碧辉煌,展示牌上写着:中国国粹,橱窗上贴着:为庆祝中秋佳节,本公司定于本月22号23号两天凡到本公司耍乐者,敬送月饼乙盒聊表心意。永旺麻雀娱乐公司启。
路过一间小便利店,一群伊斯兰小姑娘,风风火火、唧唧喳喳地拥进来,又跑出去,衣服真是好看:最大的女孩有十三四岁,穿着棕色的长裤、棕色金花的长衣、戴与长衣一样的头巾;比她小一两岁女孩则穿蓝色系列;再小的穿浅蓝色,但她的白色头巾仅披在肩上,上衣裹得不那么紧,挖着像伊斯兰教堂穹顶那样的领子;更小的女孩穿的是红衣裤,她的上衣短而且有点像裙子那样张着,衣领开口也更大,而且没有头巾;倒数第二大的女孩则直接穿一身短袖短款的白裙子;坐在儿童车里的最小的女孩干脆穿吊带裙,黄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