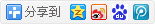离开曾大屋,步行至车公庙,大约走了有半个小时,天热又正是中午,摆卦摊的不是在打瞌睡,就是在吃盒饭,庙前偶有几个烧香的,与新年期间的热闹判若云泥,这庙是新盖的,很大,现在更是显得宽阔无比。高大的新庙后面是从前的小庙,我想转到后面,却见游客止步,左右无人,溜进去,两庙贴得太近,没有什么角度可以换,再说也不容我多选,才照一张,便有人前来阻挡。为什么不让人进原先的庙呢?他们的理由是那是古迹要保护,我觉得是怕新的神仙不被认可。
照着网友的介绍,继续向前走,直接进东铁线的大围站,省得乘马铁线一站还要换东铁线。一路转车至钻石山,找有名的志莲净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地图册上没有它,好在指示牌清楚。介绍说这里是佛教女众十方丛林,这我还真看不出来,只是另一个广告招牌:仿唐建筑比较明显,占地宽,间架大,体量厚重。不知道是因为中午,还是寺规严格,不像杂祀那样香火繁盛,背景音乐是轻声的念诵佛号,大有不识人间烟火之感,我这凡人还是有点不习惯,匆匆转了一圈就出来了。
钻石山到黄大仙只有一站,乘港铁肯定不合算,步行,中途坐在一家凉茶店里喝了一碗凉茶,大约2点钟到了黄大仙,正赶上办庙会,人多得来了不少警察,东拦西拦,跟着人走,最终我也不知道大门在哪里,怎么进的怎么出的。在这里我终于遇到了祖国大陆的旅行团,当地的人也不少,警察说庙会是派票,几周前就派完了,不过远远看去,没有遮拦的舞台上正在耍着变脸。庙会的主题:贺祖国甲子纪庆,迎建太岁元辰殿,香港人也真能整,这两块怎么给拉到一起了呢?此处的闹与一箭地之外志莲净苑的静,真是太大反差。
在网上查到过一位长者的香港游记,对从黄大仙去九龙寨城的路线写得非常详细,我就依着他所说的:“出黄大仙后从地铁B出口下去,过马路,从地铁C出口上去,就是一个小巴广场。”不过没有马上乘去旺角的小巴,因为中间隔着个7-11店,正好两边全是玻璃,能看到车站,放心地吃了冰棍,享受一阵空调。
吃冰棍期间打听了,收银员指定一条线路,告诉我跟司机说到街市下车,过了就不只三块钱了。后来发现,街市实际上过了我要去的杨侯庙,不得不打回转,这是我贪便宜的又一例。这趟去旺角的小巴八达通不可用,司机面前放了一个放硬币的盒子,像以前银行里数钢镚的,依了不同额度硬币的大小分格,乘客交了钱,司机一放即了然你给的数够不够。前面玻璃下还插着标价的牌子,开始有两块长条的牌子,一是“街市3元”,一是“旺角6元”,将到我下车之前,司机把到街市的那块牌子放倒,换了一块,我想应该是“旺角3元”吧。
街市下车,看地图往回走,杨侯庙在香港很多,但这一座是一定要去的,因为宋皇台就在附近,这杨侯是宋末忠臣杨亮节,追随宋室至香港,带病坚持工作,直至身故,受到后人的敬仰,建庙奉祀。这庙在一处高坡上,让人仰望,在香港就算是有气势的了。庙边有清静的小跨院,新修了几块诗碑,转到后面有“一笔鹤”,光绪年间刻的,因此地旧名鹤岭,与庙后身几乎贴紧,显得很局促,笔画很粗壮,也看不出是几笔。据说还有“一笔鹅”,抗战时期被日本人毁了,可能是开山取石修启德机场吧。
不远处便是九龙寨城,在我的地图册上这样写:九龙城砦Kowloon Walled City。该城几乎贴近界限街,1898年租借界限街以北领土时,订明该城寨并不包括在內,清政府在租出新界后,还曾在这里修城并派兵,然而毕竟孤悬于外,多次冲突后,终于力不能及。要说这洋人倒也守约,对此地绝不染指,不搞蚕食,任其自生自灭,在介绍中有此地老人的回忆,据说十几层的高楼不打地基,楼群更是密不透风,人人担心火灾甚至塌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英就香港问题开始谈判,一直是这城的主人中国说了:拆!建公园。英国人就赶紧干活,楞把这城改为江南园林风格的公园,为此还拿了什么国际性的设计奖,1995年底正式免费开放。
茅盾在太平洋战争暴发后从香港撤退到内地,于1943年2月在重庆写的《归途杂拾》中第一部分便是“九龙道上”。第一段就提到这里:“所谓九龙城,其实是小山顶上的一个寨,周围不过三四里,城内除了几排破房子便是一片荒地,除了住在破房子里的一两户穷人,根本无所谓居民,可是这一个荒凉的去处却是九龙租界地中间一块中国的国土。整个九龙半岛都租借去了,为什么还保留这几亩的地皮?据说也是有理由的,可是想想总觉得近乎开玩笑。九龙城的城墙倒很整齐,不用说,这已不是原物,香港政府特地花钱修葺过了。有四个城门,其中的一个(大概是东门),还有一条广阔整齐的石路,对着城门,有两尊旧式的废炮。这么一个小城,——不,一个城壳子,比上海租界内的天后宫小得多了,而且根本没有居民,当然也无从派用场。不过抗战以后,在香港拍的一部抗战影片到底将这九龙城用了一次。”
如今小山也没有了,那几排破房子大约就是现在作为展室的衙门,介绍中说这是唯一保留下来的古建筑物。衙门的门楣上,刻着并用黑漆描了“ALMSHOUSE”,翻译的话是救济院、贫民所,其实它有个中文的名字叫做“广荫院”,是当时用这片废弃房舍成立的接纳居无定所穷人的机构。门两边的对联是隶书:卤母不能臣域外龙儿幽恨敢随孤梦去,离人应已老村中燕子多情还觅故城来。恰是应了这块相当飞地的寨城的命运。落款“何文汇撰”是行书,书写者的名字用草书写,看不清尊姓大名,不知道是何时留下来的。
在修公园的时候还挖出来写有“南门”的石额,镶在了墙上,还有一块出土的石碑写的是“九龙寨城”,证明一直喊的“九龙城寨”是错误的。其余都是什么“八径异趣”(不同小径种不同的植物)、“生肖倩影”(雕有十二生肖像的园子),果然一派公园的气象,正是介绍中说的:是港人假日举家同游的选择。茅盾说的:“旅客们游玩九龙,好像有一个公式:九龙城,宋皇台,这是最先去的地方。倒不是因为这两处是古迹,而是因为最近中国已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游这两处,表示游玩之中不忘爱国。”已经过时了。
九龙寨城公园其实是贾炳达公园的一角,公园边还有条道叫做贾炳达道,我一直以为是为纪念贾姓名流呢,后来才知道原来这地方是因为聚集了不少木器作坊,被英国人称为Carpenter Road(木匠道),因为用了个“贾”字,太像个人名了。贾炳达公园的的确确是个大市民公园,一个大广场上正在搭大棚,前面的牌楼已经建好:大长陇乡建醮盛会,下面写着:萃涣堂,肯定是某个姓氏举办的,他们没有世居的小圈子,只好在公共场所办族中大事,向政府申请或者再交点费用即可使用指定区域,新加坡就是这样。大棚的对面是一座传统式样的建筑,也是临时性的,估计是举行仪式的地方,而大棚一定是戏台了。
出了贾炳达公园,沿打鼓岭道向南到头,是数条路的交汇处,界限街、太子道、亚皆老道、巴头涌道、世运道,总之一个乱字。横穿过去右拐,东边是一片空场,那是风光不再的启德机场,好像变成了旧汽车的展览场所。行人少,车速快,路边绿化多,仿佛到了郊区,走到垂直于世运道的幸运道口,望见一座中式的教堂,据地图所示,我知道宋皇台就在前面了。茅盾在《归途杂拾》也写到了:“至于宋皇台,以前香港政府也把它列为名胜之区。这里并没有台,只是一个近海的高起上有两块光秃秃的大岩石。原也有点奇怪,这两块大岩石一上一下,好像是人工叠起来似的,上面那一块大些,因而石檐之下可容一二人蜷伏。据说南宋的末代皇帝,就在这石檐下住过几宿。但我觉得这一个传说,未必可靠。帝昺当初逃到九龙,似乎还不至于窘迫到栖身在岩石罅中,如果为了躲避蒙古的追兵,则如此光秃秃的石缝,也不是个躲藏的好地方;除非那时这里的地形还不是现在那样一无遮盖,连大树也没有一株。”
现在的景象完全不同于茅盾所见,如今被称做“宋皇台公园”的所在,距离原址有一段距离,原来的山石,在茅盾仓皇奔回内地后,已经被日本人炸毁,用以扩建启德机场,所幸“宋王台”三字尚在,后来被移来此地,环以绿地,改作公园。缘何竖着“宋王台”三字碑的公园叫做“宋皇台公园”呢?公园中有一通香港赵氏宗族所立的碑记做了说明:“宋王台”三字为清代所书,沿承元史的意识,而端帝昺履此地是为中国南土之一隅,当为“皇”。又是一字之差,可见立场!
回到马头涌道上,车子很多,挨着看牌儿,发现有一趟2A小巴至宝其利街,同一站牌上的2路就不到,不放心问一位等车的妇女,正好她也做2A,认真地给我解释,并指导我上车、拍卡,听说我去红磡的观音庙,她说好灵的,车过北帝庙,还特意指给我看。车到宝其利街,她和我一起下车,说自己也要到街边的街市去买点菜。顺着她的指引向径直向观音庙去,这时已经5点半了,“庙祝”们又在擦油灯了,看来是一套程序呢。忽然急匆匆走进来一个斜背着书包的小伙子,掏钱,包红包,在观音像前上香,并把红包在飘着烟的香上面绕了几绕,把红包放进自己的钱夹,又匆匆离开了。也许今天是他的生日?或者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办,比如求职、相亲,或者办成功了?总之,他是真的信,否则何苦来走个形式呢,又没有人逼着,时间又紧张,大概是利用下班的时间来的。
找福德祠,最初制订计划是这样的:下直通车先去宝其利街上的红磡福德祠拜拜一方土地再开始香港游,但找了许多书和网,都没有明确的福德祠的位置。我的地图册上观音庙虽然没有写明,但画了一座小庙,google地图上写了观音庙,就是这个位置,我做了注释,但红磡福德祠连google地图上都没有。街边来碗陈皮红豆沙,顺便问福德祠怎么走,边走边吃,沿宝其利街向东。远远望去是个丁字路口呀,正顶着宝其利街的正是福德祠!要不是外面加盖的“大”殿,那福德祠真真正正是个小土地庙,小到盘香最得点在旁边,偏偏又坐在大街边上,街的护栏把它挤得只能侧身进入。据说这座祠建于宋末,红磡的新旧居民始终供奉,即使在当局开发红磡时,街坊也力保此庙,迫使当局承认它依原状合法存在。
已经6点了,天开始暗下来,无论在什么地方,即使在家,只要天一黑,我就得张罗回家(旅馆),还真是农民出身。这里是红磡,我知道该找东铁的终点站,像刚到香港那样,回到太子的三十六酒店,可以又遇到条条不正的街道,照理说这一带除了街歪,还算是方正,不知道是街窄人多标识物少,还是人生地不熟,总之又转向了。只好问人,这次是问一个小女孩,大约十来岁,戴眼镜、穿粉格裙,不像是校服,所以可能不是才放学的,空着两手,也不是被差出来打酱油的。她告诉我这么走那么拐,讲得挺清楚,咱也礼貌道了谢,一路下去两三个街区,果然看到她说的天桥。
刚走到天桥的台阶下,有人从后面捅捅了我的后肘,虽说香港街上人多,不免有碰撞,但这一下不像,马上警觉起来,回头一看,竟是刚才指路的女孩,她微笑着:就上这座桥,一直走就对了。我吃惊地问:你一直追我这么远?她点头:我怕你走错了,有很多出口的。你能相像我当时的感动吗?我这人不算太热心,但遇到问路,也是蛮认真对待,不知道的还颇不好意思,但总觉得自己没讲明白,到下一段人家自会向别人问询,绝没有想到要负责到底。
这女孩的态度,可不是我再三再四地道谢所能回报的,随着她扬手说拜拜,这么多天来帮助过我的那些女人全都叠加在她的身上。我一下子爱上香港,不只是来之前就期待已久的,冰冷的或热络的神仙,鼎鼎大名的和默默无闻的神仙,挤在城市里与散在乡村间的神仙,高居庙堂之上同蹲守陋室之角的神仙,更意外地收获了香港平凡的和气,平淡的诚恳,平常的关怀,平静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