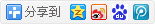《香江随笔》之七:
我所认识的香港人
作者:枫之岭 http://blog.sina.com.cn/wildmapleridge
(更多内容与图片,请见“枫之岭”新浪博客)
在派驻香港工作之前,我对香港人缺乏实际了解,毕竟北京与香港远隔千山万水,在北京难得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香港人,北京人对香港人的印象一般来自于电影,在整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大陆影视作品中但凡出现香港人,十之八九不是奸商就是骗子,说话不仅吞吞吐吐,而且拖着长长的尾音,广东话在北京被戏称为“鸟语”。反过来,1997年之前的香港电影里,大陆人的形象也好不到哪儿去,最典型的莫过郑裕玲主演的《表姐,你好嘢!》,不仅粗鄙而且丑陋。我至今也没有搞懂,当时两地的演艺界人士为什么要相互恶意攻讦,必陷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一、语言的障碍
我对香港人的认识,首先是从语言开始的。到香港工作之前,我曾经多次去广东出差,还曾经在珠海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对于粤语虽然不算陌生,但是也是基本无法听懂,记得第一次途径香港时,由于飞机晚点耽误了转机,中国民航临时安排我们入住启德机场的富豪酒店,我在酒店大堂的商店里闲逛,一位店员小姐走过来笑吟吟地用英语问道:先生是否日本人?我支支吾吾不敢正面作答,顾左右而言他。那个年代,大陆人唯恐自己在香港遭人鄙视,从不敢讲普通话,据说在餐馆里,如果你不讲英语或广东话,都不会有人过来搭理你。
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不懂香港话显然不行,九十年代初期普通话还不流行,因此,每天下班回宿舍后的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电视,开始只是看一些简单的新闻节目,最喜欢看的是无线明珠台的930节目,这个时段的英文电影特别好看又有中文字幕,理解起来比较容易,最烦的节目就是插科打诨式的娱乐性谈话节目,内容基本无法听懂,觉得这类节目完全就是臭贫。刚到香港时,与当地人沟通十分困难,基本是“鸡同鸭讲”,各说各话,不过好在公司里的香港员工基本都能讲普通话,交流起来没有问题。大约是过了半年左右时间,我能听懂大部分粤语了,逐渐开始讲一些简单的词句,才逐渐发现粤语其实非常幽默,一点儿不弱于相声中的北京话、天津话,小品中的东北话。
二、文明、礼貌、遵守公共秩序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香港人就给我留下了一个文明、礼貌和遵守秩序的印象。公众场所基本见不到有人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人们在巴士站、地铁站、码头从来都是自觉排队,没有人插队、拥挤,有时地铁上、下班高峰时段,排队的乘客一直从站台排到站外的街道上,见到已经有人排队,后面新来的人就会自觉地停下脚步,绝少见到北京地铁站里那种拥挤、推撞、争吵的混乱场面。车上很少有人抢占座位,大多数人都会主动给行动不便的人让位。有人过马路上的人行道时,司机会停下车让路。我在香港生活几年,从未在街上见到争吵、打架的现象。记得有一年参加香港的“百万行”活动,各路人马在维园集合时,有一个公司免费派发体恤衫,只有两箱体恤衫,可队伍却越排越长,许多人明明知道无望领到还在安静地排队,实在令人佩服。
三、良好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
我所在的公司是香港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承建了许多政府大型公共工程,在那个年代,香港还处于英国管制,大陆的学历和资质都得不到承认,中文也没有法律地位,大陆内派人员只能从事公司内部管理,所有专业技术工作、对外联络均由香港员工负责,是工程项目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
我刚到香港时被分到一处工地见习,经理交代我先熟悉工程文件,凡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向地盘代表请教,我对建筑上的基本概念还算了解,英文也不是一个问题,主要的困难是对英国的建筑规范、BS标准一无所知,每当遇到一些技术问题时代表都能耐心解答,有时还会找来地盘工程师、地盘总管一起讨论,使我受益匪浅。
除了良好的专业素养之外,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则是香港同事体现的敬业精神。九十年代初期,大陆还未完全脱离大锅饭时代,许多人出工不出力,在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里,工作推诿敷衍,上班一杯茶、一份报,以闲聊、神侃打发时间,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在香港,我们虽然是内资企业,却看不到这样的情景,根本无须领导督促,大部分香港员工都会自觉工作,许多人甚至追求尽善尽美,实在令人敬佩。
四、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我对香港人的另一个印象就是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香港是一个节奏极快的地方,街上车辆川流不息,人们步履匆匆,地铁的自动扶梯本来已经极快,但许多人仍然还要在上面奔跑。香港同时还是一个生活充满压力的地方,没有失业保险和退休金,寸土寸金,生活费用昂贵,许多年轻人要打几分工养家糊口;老年人仍要辛苦劳作,为生存而奔波,但香港人仍然保持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
在香港工作的第二年,我争取到一个到香港大学业余进修的机会。每天收工之后,我要立即赶到港大在港岛或尖沙咀的校区上课,从晚上七点钟一直要上课到九点半。在读书期间,我结识了许许多多的香港年轻人,才明白原来有那么多的年轻人,都在利用一切空余时间来充实自己。
当然,我也在一定程度上,也使香港人改变了对大陆人的看法,刚入港大读书时,当同学们听说我来自北京时都异常惊讶,怎么会有大陆人胆敢来港大读书!另一个好笑的事情是:第一门课考试前的最后一次复习课,老师讲完课走到每个同学面前,询问是否有什么问题,平时他都用英语讲课,此时他改用香港话与学生交谈,当他走到我的座位前与我交谈时,忽然发现我是从北京来的,便吃惊地问:“我在港大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碰到过大陆来的学生,你能跟得上课吗?英文能听得懂吗?”我表示没有问题,他似乎有些将信将疑。不过,后来可以验证的结果是:我是一次通过了全部八门课程,以最短的时间拿到了毕业证书,我周围的同学很少能够做到,至少,大陆人在读书上不会输给香港人。
五、相互来往可以增加了解、消除隔阂
在香港几年的工作和生活,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香港人,现在看来许多成见、误解都来自于相互不了解。其实,香港人是由不同的群体组成的,除了世世代代在香港居住的当地人,有许多人实际是大陆来的新移民。
近几十年间,大陆有几次大规模的香港移民潮:一次是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大量难民涌入香港,北角一带几乎由江浙人占领,至今还保留着一些上海的传统和遗风;另一次是六十年代初期的大饥荒,许多人逃亡香港活命,直到八十年代,九龙和新界一带还有不少成片的寮屋区;从七十年代开始直至九十年代,有不少大陆人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以偷渡或移民的方式进入香港。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最先回到家乡的投资的港商,就是这些七十、八十年代来到香港的大陆人,他们本身并未进入香港主流社会,亦没有资金实力,但却非常了解大陆的政策,擅长利源法律、制度上的漏洞钻营取巧,所以给大陆人留下了“香港人都是骗子”的印象。
随着对香港了解的深入,我才发现其实许多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从未去过大陆,几乎不了解大陆的变化。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例子是:我们公司每年在深圳人民医院为全体员工组织一次免费体检,香港员工基本不去,宁可自己花钱在香港本地医院做体检,问他们为什么不去时,一些人对我表示不信任国内医院的卫生条件,还有不少人干脆告诉我自己从来不去大陆,那里太乱不敢去!越是香港出生、长大的人越是如此,凡是度假都是去美、日、欧,或新、马、泰。
当时大陆内派工作人员对香港人缺少足够的了解,即使在中资机构内部大陆人与本地员工之间,工作时间以外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来往,内派干部一般都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有自己的食堂,又受到外事纪律的约束,平时接触的都是自己人。我有一个北京朋友在外交部驻港签证处工作,工作地点在湾仔的华润大厦,上班时关在封闭的柜台里,几乎接触不到香港人,下班坐叮当车回跑马地的外交部宿舍,天天如此,只有在周末时才逛逛北角,两年下来连香港的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可见当时是多么封闭。
我在香港那几年,正是政权交接开始进入倒计时的年代,许多香港人感到彷徨,对自己的前途焦虑不安,社会阶层开始迅速分化,一部分政商人士开始向大陆靠拢,一些大商人开始积极进军大陆寻找商机;另有一些人借助港英当局的庇护,继续作顽强的抵抗,政治冲突渐渐激烈;但更多的黎民百姓面对前途纷争,显得全然无助,就像罗大佑的那首歌《皇后大道东》中表露出的那样一种彷徨、焦虑的情绪,香港前途似乎是中、英两国政府间的事情,香港人完全无法插手,就像儿女的婚姻由双方父母操办,当事人自己无权过问那样,香港人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遗憾的是,这样的政治纷争依然困扰香港,而且还有愈发严重的趋势。
不过,1997是一个分水岭,不论你是否喜欢,也没人问你是否愿意,香港人和大陆人已经推到了彼此之间人为筑起的墙,随着政权的交替和人民的往来,香港人与大陆人已经渐渐融为一体,电影里那种那对方开涮的场景已经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普通话已经成为香港人的通用语言,在这场巨大的变革中,但愿香港人还能守住自己的价值,能够引领全体中国人走向一个更加文明的阶段。
(更多内容与图片,请见“枫之岭”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wildmapleri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