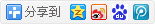茶马古道上的苏州风韵
茶马古道上的苏州风韵
和建国从石莲寺下来,穿过村子,慢吞吞地沿着清澈得不行的小河沟,偶尔见到一两个村里的居民,背着刚收的萝卜,新鲜的萝卜缨子,很想尝尝,用芥末拌拌生吃,一定味道很好。。。从小就对美的东西没有没免疫力,美食、美景、精致的东西。
正想得口水流的时候,建国的声音飘到耳朵里: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大石头路,是当年纳西马锅头赶着马队去贩茶的路。
“哦? 马锅头在哪里?哪里?
你傻了呀?马锅头是百年以前在这路上走,走的多了,马蹄印就留在这些大石头上了。
突发奇想,拖着建国沿着马蹄印想看看能走出这村子吗?还是会是去西藏的茶马古道?
在一个土屋的转角,马蹄印消失了,又看到了刚才那条清澈的不行的小河沟,但是古道没了,一条新修的石头?!不会吧?!站在古道和新石头路的交汇处,带着希望,四处张望,想再看到古道出现在石头路的另一侧。
咦?新石头路的尽头,一个苏州园林中的匾额,,遮掩在一丛翠竹旁:石莲精舍。客栈?不像,这么安静的地方,行人罕至;村里的民居?古朴的样子和村里的其他宅子一样,好像百年前就站在这儿了。可是,挑高的檐角,白墙黑瓦,又透出精致的韵味。
奇了。犹豫着,雀跃着。
走,去看看!
建国倒是干脆,一把拖着我兴冲冲地冲到半掩着的墨黑的木头大门外。
还是不去了吧,看起来好像是别人家。
没关系的,这家人半开着门,就是欢迎之意。走,进去。
刚还在惊讶于门廊处的透着古意的几案和匾额,一转角,一株玉兰,婷婷站在小院子中间,几条小鱼在玉兰树下的河沟里很自在,墙边立着一个通透的玻璃茶屋,茶屋里,对着笔记本电脑的一个男孩子抬起眼瞅瞅我们,低下头,继续在电脑上写着什么。正对面一个两层的阁楼,白墙黑瓦,黑底绿字的对联,一个大福娃挂在墙上,笑嘻嘻的瞧着我。
主人家在吗?建国扬声问道。
一个身着白衫,手握一卷书的男子应声而出,看去,四十岁左右。“你们有什么事吗?”他温和地问道。
石莲精舍,这是您家吗?还是您的客栈啊?我们在门外忍不住就想进来看看,可以吗?我满脸的的期待地看着他。心里有些忐忑,第一次这样很雀跃地不请自入,觉得有些不妥,可是还是忍不住期待地看着他。
他就是三石。现在当我回忆起初见三石的时候还想笑,因为啊,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是四十岁,而是二十五岁,他不是精舍的老板,却是方外之士;精舍是客栈,可却不仅仅是客栈。
而我们这样的推门而入,就一脚从束河这个茶马古道上的村落踏进了千里之外同样古老的苏州。
我和建国坐在茶室里。对面是精舍的主人,布衣。
布衣,石莲精舍的主人,原本经营了苏州同里正福草堂客栈多年,某日来到束河一游,却因着实喜欢这个茶马古道上纳西村庄的古朴雅静和九鼎龙潭泉水的清澈,索性觅得这古村落里的几处宅院停留了下来;
因常有同样喜欢寻古觅静的客人也希望在此停留,所以在村里百年前的马帮张锅头老宅中造了名为可心小筑的客栈。而在从九鼎龙潭流下的小溪上的纳西民居中,则建了石上流泉-草堂素食餐馆。其中一处自住的宅院,造在了石莲寺山脚下,夜夜听得石莲夜读声,名为石莲精舍。
转眼在这个九鼎龙潭下的村子, 布衣已住了一年多,和朋友,甚或像我们这样推门而入的客人一道,时时品茗,听琴,唱苏州评弹,谈佛家心得,我想,神仙的日子,就是这样啦。
坐在精舍的茶室中,听着布衣、三石和建国他们在谈着精舍、石上流泉和草堂素食的由来,心思已经不在飘着香味的武夷大红袍上面,忍不住脱口而出,我很想去看看这几个另宅院可以吗?
可以的,布衣仍然是初见他时的宽容和谦和的笑容。
还是先看看精舍---
出了茶室,上了槛月楼,楼上客房是一些老友或客人来时休息用的。进入房间,被墙边红色卧榻上方的小幅绢画吸引,看了很久,心里喜欢的很,一问,得知墙上这些画是宋小品。而线条简洁的红色美人榻和墙角的柜子,竟然来自千里外的苏州。
槛月楼的对面,是另一处小楼,听说楼上是布衣他们参禅拜佛的禅室,楼下则是平日抚琴的地方。
禅室是修行的地方,我虽然好奇,可是也知道不可以随意打扰佛堂的清净,于是进了楼下的琴室。好一处雅静的之处!左侧尽头处琴台上一古琴安放,琴前香炉轻烟缭缭。在旅途中,我好动的因子是被张扬到了极限的,可是在这个琴室中,却和其他人一样,默然,不知伯牙今夕何在?
朴实内敛,翠竹依门.
和建国从石莲寺下来,穿过村子,慢吞吞地沿着清澈得不行的小河沟,偶尔见到一两个村里的居民,背着刚收的萝卜,新鲜的萝卜缨子,很想尝尝,用芥末拌拌生吃,一定味道很好。。。从小就对美的东西没有没免疫力,美食、美景、精致的东西。
正想得口水流的时候,建国的声音飘到耳朵里: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大石头路,是当年纳西马锅头赶着马队去贩茶的路。
“哦? 马锅头在哪里?哪里?
你傻了呀?马锅头是百年以前在这路上走,走的多了,马蹄印就留在这些大石头上了。
突发奇想,拖着建国沿着马蹄印想看看能走出这村子吗?还是会是去西藏的茶马古道?
在一个土屋的转角,马蹄印消失了,又看到了刚才那条清澈的不行的小河沟,但是古道没了,一条新修的石头?!不会吧?!站在古道和新石头路的交汇处,带着希望,四处张望,想再看到古道出现在石头路的另一侧。
咦?新石头路的尽头,一个苏州园林中的匾额,,遮掩在一丛翠竹旁:石莲精舍。客栈?不像,这么安静的地方,行人罕至;村里的民居?古朴的样子和村里的其他宅子一样,好像百年前就站在这儿了。可是,挑高的檐角,白墙黑瓦,又透出精致的韵味。
奇了。犹豫着,雀跃着。
走,去看看!
建国倒是干脆,一把拖着我兴冲冲地冲到半掩着的墨黑的木头大门外。
还是不去了吧,看起来好像是别人家。
没关系的,这家人半开着门,就是欢迎之意。走,进去。
刚还在惊讶于门廊处的透着古意的几案和匾额,一转角,一株玉兰,婷婷站在小院子中间,几条小鱼在玉兰树下的河沟里很自在,墙边立着一个通透的玻璃茶屋,茶屋里,对着笔记本电脑的一个男孩子抬起眼瞅瞅我们,低下头,继续在电脑上写着什么。正对面一个两层的阁楼,白墙黑瓦,黑底绿字的对联,一个大福娃挂在墙上,笑嘻嘻的瞧着我。
主人家在吗?建国扬声问道。
一个身着白衫,手握一卷书的男子应声而出,看去,四十岁左右。“你们有什么事吗?”他温和地问道。
石莲精舍,这是您家吗?还是您的客栈啊?我们在门外忍不住就想进来看看,可以吗?我满脸的的期待地看着他。心里有些忐忑,第一次这样很雀跃地不请自入,觉得有些不妥,可是还是忍不住期待地看着他。
他就是三石。现在当我回忆起初见三石的时候还想笑,因为啊,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是四十岁,而是二十五岁,他不是精舍的老板,却是方外之士;精舍是客栈,可却不仅仅是客栈。
而我们这样的推门而入,就一脚从束河这个茶马古道上的村落踏进了千里之外同样古老的苏州。
我和建国坐在茶室里。对面是精舍的主人,布衣。
布衣,石莲精舍的主人,原本经营了苏州同里正福草堂客栈多年,某日来到束河一游,却因着实喜欢这个茶马古道上纳西村庄的古朴雅静和九鼎龙潭泉水的清澈,索性觅得这古村落里的几处宅院停留了下来;
因常有同样喜欢寻古觅静的客人也希望在此停留,所以在村里百年前的马帮张锅头老宅中造了名为可心小筑的客栈。而在从九鼎龙潭流下的小溪上的纳西民居中,则建了石上流泉-草堂素食餐馆。其中一处自住的宅院,造在了石莲寺山脚下,夜夜听得石莲夜读声,名为石莲精舍。
转眼在这个九鼎龙潭下的村子, 布衣已住了一年多,和朋友,甚或像我们这样推门而入的客人一道,时时品茗,听琴,唱苏州评弹,谈佛家心得,我想,神仙的日子,就是这样啦。
坐在精舍的茶室中,听着布衣、三石和建国他们在谈着精舍、石上流泉和草堂素食的由来,心思已经不在飘着香味的武夷大红袍上面,忍不住脱口而出,我很想去看看这几个另宅院可以吗?
可以的,布衣仍然是初见他时的宽容和谦和的笑容。
还是先看看精舍---
出了茶室,上了槛月楼,楼上客房是一些老友或客人来时休息用的。进入房间,被墙边红色卧榻上方的小幅绢画吸引,看了很久,心里喜欢的很,一问,得知墙上这些画是宋小品。而线条简洁的红色美人榻和墙角的柜子,竟然来自千里外的苏州。
槛月楼的对面,是另一处小楼,听说楼上是布衣他们参禅拜佛的禅室,楼下则是平日抚琴的地方。
禅室是修行的地方,我虽然好奇,可是也知道不可以随意打扰佛堂的清净,于是进了楼下的琴室。好一处雅静的之处!左侧尽头处琴台上一古琴安放,琴前香炉轻烟缭缭。在旅途中,我好动的因子是被张扬到了极限的,可是在这个琴室中,却和其他人一样,默然,不知伯牙今夕何在?
朴实内敛,翠竹依门.